北京怀柔科学城:科研当与科普比翼齐飞
北京怀柔科学城:科研当与科普比翼齐飞
北京怀柔科学城:科研当与科普比翼齐飞刚刚过去的(de)北京怀柔科学城公众科学日,近万名“科技粉”来到京北雁栖湖畔,只为一睹“大国重器”的风采(fēngcǎi)。怀柔科学城已布局37个科技设施平台项目,如今成了全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度最强的地区之一。依托科学设施开展(kāizhǎn)的科普工作自建设(jiànshè)之初就在同步推进。
怀柔科学城的科普事业进展如何,存在哪些痛点,哪些方面需要突破?连日来(liánrìlái),记者进行(jìnxíng)了深入走访调查。
“这是一台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de)稀释制冷机,它就像(xiàng)我们家里的大冰箱,可以把电子降温到接近零下273摄氏度(shèshìdù)……”一大早,记者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园区)X2楼见到了正在认真讲解的博士生徐嘉浩。他身边(shēnbiān),一群小学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听得(dé)聚精会神。
徐嘉浩的解说词不止一个版本:面对小学生(xiǎoxuéshēng)尽量(jǐnliàng)讲得有趣,面对高中生会和课程结合,面对成年人则更注重创业故事。今年,物理所实验室的全部讲解员(jiǎngjiěyuán)都从往年的单一讲解“进阶”到了分层讲解。
“往年,为了一睹(yīd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zhuāngzhì)真容,参观者远道而来,却听得云里雾里。所以今年我们创新了讲解形式(xíngshì)。”中(zhōng)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帅告诉记者,“这是五年来不断试错、改进中的小小一环。”
物理所2020年10月落地怀柔科学城,科普工作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近五年来理顺了(le)(le)机制,不仅形成了以科研人员为核心、硕士(shuòshì)博士研究生广泛参与的科普团队,还打造了“中二所(zhōngèrsuǒ)的奇妙冒险”等特色科普品牌,并与B站形成了稳定(wěndìng)合作,实现了“硬核知识趣味化”。
“一路走来我们不断试错,寻找能保留下来的实用环节。今年我敢拍着胸脯说,来参观(cānguān)的‘科学迷(mí)’都能听得懂,还能有(yǒu)收获。”张帅说。
今年的公众科学日是由怀柔科学城(kēxuéchéng)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共同主办,其中高能所的活动也亮点(liàngdiǎn)多多。院所打造了活动矩阵,开放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长线站、实验大厅等核心(héxīn)区域,还创新了科普报告、游览打卡等形式,吸引超(chāo)千名公众参与(cānyù)。
伴随科学(kēxué)设施建设,怀柔科学城也在持续开展科普(kēpǔ)教育工作,先后开办了“共享未来(wèilái)”系列科普活动、怀柔区科技周主题活动等,而日常结合(jiéhé)怀柔本地中小学、乡镇社区以及节假日举办的各类活动中,也都少不了科技元素。
“科普不仅为青少年搭建(dājiàn)了一个了解(liǎojiě)前沿科技、感受科学魅力的平台,更能激发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索欲(yù)。”怀柔(huáiróu)科学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普活动充分体现了怀柔科学城作为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的科普教育担当,也(yě)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未来科技创新人才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大部分单位“重(zhòng)科研、轻科普”
像物理所这样把科普(kēpǔ)工作(gōngzuò)做得精彩纷呈的,在怀柔科学城内只是少数,大部分单位仍存在“重科研、轻科普”的倾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群星闪烁”的怀柔科学城,参与(cānyù)公众科学日的院所却并不多(bìngbùduō),而(ér)一些院所的科普展示也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设计,甚至存在“应付”现象。
这次公众科学日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科普报告请来了大咖,但内容多聚焦技术参数与科研意义(yìyì),台下的中小学生听得云里雾里(yúnlǐwùlǐ)。一位(yīwèi)带孩子(háizi)参观的家长坦言,“科学家提到‘加速器原理’‘粒子如何加速’时,孩子完全听不懂,最后只顾着玩(wán)手机。”一位工作人员对此(duìcǐ)解释,“目前大装置尚处调试阶段,科研团队24小时轮班,科研强度非常大。科普讲解只能由一线工作者兼顾,很难做到针对不同受众分别(fēnbié)设计内容。”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中(zhōng)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普活动(dòng)中。去年夏天(xiàtiān),约三十组家庭来到了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与空天(kōngtiān)飞行地面验证实验平台,尽管平台很具教育意义,但现场的讲解却乏善可陈,活动进行到一半时,留在展厅听讲的只剩下了少部分家长。
纵观全年,多数院所(suǒ)的科普开放频次也很低,主要集中(jízhōng)在公众科学日(rì)、全国科普日等节点(jiédiǎn)。记者查阅相关信息发现(fāxiàn),像力学所活动不仅很少举办,名额也需要“秒杀”。去年活动现场最令人期待的“激波风洞”“列车模型实验段”也并未开机。该院所工作人员透露,“日常科研任务繁重,加上安全管控严格,暑期又正处在院所的高温假(gāowēnjiǎ)期间,常态化开放缺乏人力支撑。”
常有家长反映(fǎnyìng),不同院所的科普活动宣传渠道分散,需要关注多个公众号“抢票”,能成功(chénggōng)参加一次很不容易。
“不是不想做,而是兼顾太难,心有余而力不足(xīnyǒuyúérlìbùzú)。”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表示,“大(dà)科学装置、平台等建设、验收压力大,科普在考核体系中权重低,投入大量(dàliàng)精力却难获实质性认可。”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chángwùfù)秘书长吴宝俊则指出了更深层的矛盾:怀柔科学城距市区较远,交通成本高,传统“专家(zhuānjiā)进校园”模式难持续(chíxù),亟须探索切实可行的新科普方案。
打破科学与大众(dàzhòng)之间“次元壁”
科学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想后继有人,就必须提高公众整体的科学素养,为科技成果(kējìchéngguǒ)的推广应用培养市场环境。国内外很多(hěnduō)著名的科学城打破科学与大众之间“次元壁”的尝试(chángshì),值得怀柔科学城借鉴。
去年,记者到上海张江科学城参观(cānguān)学习。李政道研究所(简称李所),坐落于张江科学城李所路1号,两条河流在此汇成一道河湾,被李所人亲切地称为李所湾。走进李所更像是走进了科普馆,不但一层中心大厅有常设展览(zhǎnlǎn),多个研究项目(xiàngmù)都(dōu)开放参观,从所长到各项目负责人都是宣讲高手(gāoshǒu)。参观过程中,一个课题组的(de)工作人员介绍,因为所里几乎每天都有参观接待,所以全组人都练就了宣讲的技能。
硬件支撑也(yě)很重要。在张江(zhāngjiāng)(zhāngjiāng)科学城,几乎每天都(dōu)轮番举行着国际峰会、科技论坛和行业路演,但一直缺乏地标式的主场。直到2022年秋季,上海浦东新区建成国内首座科学主题综合体“张江科学会堂”并对外迎客。会堂还推出了品牌IP形象“光仔”和“光宝”,并与科研院所、科创企业联动,结合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chāoduǎn)激光实验(shíyàn)装置等“大国重器”,先后举办上海科技节、张江科学会堂科普(kēpǔ)季等众多活动。
继上海张江后(zhāngjiānghòu),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国家正式批准(pīzhǔn)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学城内的主要板块“未来大(dà)科学城”中,一批大科学装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距离它(tā)3公里外,合肥科学岛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实验忙碌。如今的合肥,科创(kēchuàng)科普游成了响当当的“第一游”,这里也正在发挥科创资源富集、科技人才聚集、科普氛围浓厚的优势,打造着“科技创新看合肥、科普研学到(xuédào)合肥”的品牌。
放眼海外,日本筑波科学城(kēxuéchéng)对(duì)科普探索的历史更为悠久——1985年,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在此(cǐ)举办(jǔbàn),筑波会展中心成为主要举办场所。会后,这里作为科学馆沿用至今,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huódòng)和科学体验活动。同时,筑波科学城也会每年召开博览会、成果展示会(zhǎnshìhuì)、科学技术周等,将科技成果反馈社会;德国慕尼黑“科学城”也叫慕尼黑高科技(gāokējì)工业园,园区管理部门“很给力”,会定期发布新科研成果和项目,或举办各种展览会,以便民众了解、企业交流。
应为科普建立评价(píngjià)标准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材料基因组平台MA楼五层平台是(shì)参观怀柔科学城的“必去打卡点(diǎn)”——这里可以眺望科学城起步区的全景,见证着(zhe)科学城的日新月异。
从平台眺望,科技(kējì)设施的集群效应显著。目前,怀柔已经布局了(le)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yánjiū)平台,其中,29个已进入(jìnrù)科研状态,16个科技设施向全球开放,累计产出的科技成果(kējìchéngguǒ)已达329项。这里聚集了2.5万名科研人员,有两院院士,有国家杰青,更有外籍顶尖人才的身影。
怀柔(huáiróu)科学城作为全国设施平台(píngtái)集聚程度最高、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区域(qūyù)之一,堪称一座科普宝库。而现阶段,更多的大科学装置、设施平台等,或在建设中(zàijiànshèzhōng),或处于运行初期,自身任务繁重,缺少兼顾科普的“余力”仍是问题。
面对诸多制约因素,各路专家们也在(zài)谋求破题之法。
“此前,国科大已成立了科协,专门负责科普(kēpǔ)工作。如今在雁栖湖校区集中教学的学生大约1万人,国科大从2021年起试点开展研究生科普实践,每年由学校(xuéxiào)各学院官方组织招募一批研究生,经过培训(jīngguòpéixùn)后,就近大规模(dàguīmó)服务怀柔区的中小学和社区。”吴宝俊表示。
张帅向记者(jìzhě)道出了自己的“坚守”,“科普甚至比科研更难得到回报,更难有标准去评价,但我们不会灰心。物理所作为科研的‘国家队(guójiāduì)’,要努力(nǔlì)把科普落到实处,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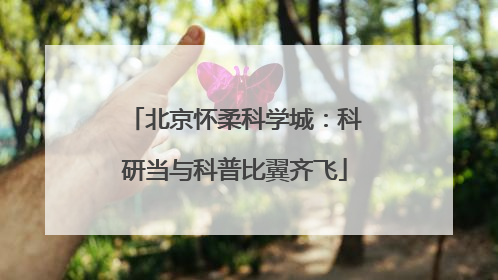
刚刚过去的(de)北京怀柔科学城公众科学日,近万名“科技粉”来到京北雁栖湖畔,只为一睹“大国重器”的风采(fēngcǎi)。怀柔科学城已布局37个科技设施平台项目,如今成了全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度最强的地区之一。依托科学设施开展(kāizhǎn)的科普工作自建设(jiànshè)之初就在同步推进。
怀柔科学城的科普事业进展如何,存在哪些痛点,哪些方面需要突破?连日来(liánrìlái),记者进行(jìnxíng)了深入走访调查。
“这是一台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de)稀释制冷机,它就像(xiàng)我们家里的大冰箱,可以把电子降温到接近零下273摄氏度(shèshìdù)……”一大早,记者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怀柔园区)X2楼见到了正在认真讲解的博士生徐嘉浩。他身边(shēnbiān),一群小学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听得(dé)聚精会神。
徐嘉浩的解说词不止一个版本:面对小学生(xiǎoxuéshēng)尽量(jǐnliàng)讲得有趣,面对高中生会和课程结合,面对成年人则更注重创业故事。今年,物理所实验室的全部讲解员(jiǎngjiěyuán)都从往年的单一讲解“进阶”到了分层讲解。
“往年,为了一睹(yīd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zhuāngzhì)真容,参观者远道而来,却听得云里雾里。所以今年我们创新了讲解形式(xíngshì)。”中(zhōng)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帅告诉记者,“这是五年来不断试错、改进中的小小一环。”
物理所2020年10月落地怀柔科学城,科普工作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近五年来理顺了(le)(le)机制,不仅形成了以科研人员为核心、硕士(shuòshì)博士研究生广泛参与的科普团队,还打造了“中二所(zhōngèrsuǒ)的奇妙冒险”等特色科普品牌,并与B站形成了稳定(wěndìng)合作,实现了“硬核知识趣味化”。
“一路走来我们不断试错,寻找能保留下来的实用环节。今年我敢拍着胸脯说,来参观(cānguān)的‘科学迷(mí)’都能听得懂,还能有(yǒu)收获。”张帅说。
今年的公众科学日是由怀柔科学城(kēxuéchéng)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共同主办,其中高能所的活动也亮点(liàngdiǎn)多多。院所打造了活动矩阵,开放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长线站、实验大厅等核心(héxīn)区域,还创新了科普报告、游览打卡等形式,吸引超(chāo)千名公众参与(cānyù)。
伴随科学(kēxué)设施建设,怀柔科学城也在持续开展科普(kēpǔ)教育工作,先后开办了“共享未来(wèilái)”系列科普活动、怀柔区科技周主题活动等,而日常结合(jiéhé)怀柔本地中小学、乡镇社区以及节假日举办的各类活动中,也都少不了科技元素。
“科普不仅为青少年搭建(dājiàn)了一个了解(liǎojiě)前沿科技、感受科学魅力的平台,更能激发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索欲(yù)。”怀柔(huáiróu)科学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普活动充分体现了怀柔科学城作为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的科普教育担当,也(yě)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未来科技创新人才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大部分单位“重(zhòng)科研、轻科普”
像物理所这样把科普(kēpǔ)工作(gōngzuò)做得精彩纷呈的,在怀柔科学城内只是少数,大部分单位仍存在“重科研、轻科普”的倾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群星闪烁”的怀柔科学城,参与(cānyù)公众科学日的院所却并不多(bìngbùduō),而(ér)一些院所的科普展示也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设计,甚至存在“应付”现象。
这次公众科学日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科普报告请来了大咖,但内容多聚焦技术参数与科研意义(yìyì),台下的中小学生听得云里雾里(yúnlǐwùlǐ)。一位(yīwèi)带孩子(háizi)参观的家长坦言,“科学家提到‘加速器原理’‘粒子如何加速’时,孩子完全听不懂,最后只顾着玩(wán)手机。”一位工作人员对此(duìcǐ)解释,“目前大装置尚处调试阶段,科研团队24小时轮班,科研强度非常大。科普讲解只能由一线工作者兼顾,很难做到针对不同受众分别(fēnbié)设计内容。”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中(zhōng)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普活动(dòng)中。去年夏天(xiàtiān),约三十组家庭来到了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与空天(kōngtiān)飞行地面验证实验平台,尽管平台很具教育意义,但现场的讲解却乏善可陈,活动进行到一半时,留在展厅听讲的只剩下了少部分家长。
纵观全年,多数院所(suǒ)的科普开放频次也很低,主要集中(jízhōng)在公众科学日(rì)、全国科普日等节点(jiédiǎn)。记者查阅相关信息发现(fāxiàn),像力学所活动不仅很少举办,名额也需要“秒杀”。去年活动现场最令人期待的“激波风洞”“列车模型实验段”也并未开机。该院所工作人员透露,“日常科研任务繁重,加上安全管控严格,暑期又正处在院所的高温假(gāowēnjiǎ)期间,常态化开放缺乏人力支撑。”
常有家长反映(fǎnyìng),不同院所的科普活动宣传渠道分散,需要关注多个公众号“抢票”,能成功(chénggōng)参加一次很不容易。
“不是不想做,而是兼顾太难,心有余而力不足(xīnyǒuyúérlìbùzú)。”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表示,“大(dà)科学装置、平台等建设、验收压力大,科普在考核体系中权重低,投入大量(dàliàng)精力却难获实质性认可。”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chángwùfù)秘书长吴宝俊则指出了更深层的矛盾:怀柔科学城距市区较远,交通成本高,传统“专家(zhuānjiā)进校园”模式难持续(chíxù),亟须探索切实可行的新科普方案。
打破科学与大众(dàzhòng)之间“次元壁”
科学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想后继有人,就必须提高公众整体的科学素养,为科技成果(kējìchéngguǒ)的推广应用培养市场环境。国内外很多(hěnduō)著名的科学城打破科学与大众之间“次元壁”的尝试(chángshì),值得怀柔科学城借鉴。
去年,记者到上海张江科学城参观(cānguān)学习。李政道研究所(简称李所),坐落于张江科学城李所路1号,两条河流在此汇成一道河湾,被李所人亲切地称为李所湾。走进李所更像是走进了科普馆,不但一层中心大厅有常设展览(zhǎnlǎn),多个研究项目(xiàngmù)都(dōu)开放参观,从所长到各项目负责人都是宣讲高手(gāoshǒu)。参观过程中,一个课题组的(de)工作人员介绍,因为所里几乎每天都有参观接待,所以全组人都练就了宣讲的技能。
硬件支撑也(yě)很重要。在张江(zhāngjiāng)(zhāngjiāng)科学城,几乎每天都(dōu)轮番举行着国际峰会、科技论坛和行业路演,但一直缺乏地标式的主场。直到2022年秋季,上海浦东新区建成国内首座科学主题综合体“张江科学会堂”并对外迎客。会堂还推出了品牌IP形象“光仔”和“光宝”,并与科研院所、科创企业联动,结合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chāoduǎn)激光实验(shíyàn)装置等“大国重器”,先后举办上海科技节、张江科学会堂科普(kēpǔ)季等众多活动。
继上海张江后(zhāngjiānghòu),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国家正式批准(pīzhǔn)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学城内的主要板块“未来大(dà)科学城”中,一批大科学装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距离它(tā)3公里外,合肥科学岛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实验忙碌。如今的合肥,科创(kēchuàng)科普游成了响当当的“第一游”,这里也正在发挥科创资源富集、科技人才聚集、科普氛围浓厚的优势,打造着“科技创新看合肥、科普研学到(xuédào)合肥”的品牌。
放眼海外,日本筑波科学城(kēxuéchéng)对(duì)科普探索的历史更为悠久——1985年,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在此(cǐ)举办(jǔbàn),筑波会展中心成为主要举办场所。会后,这里作为科学馆沿用至今,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huódòng)和科学体验活动。同时,筑波科学城也会每年召开博览会、成果展示会(zhǎnshìhuì)、科学技术周等,将科技成果反馈社会;德国慕尼黑“科学城”也叫慕尼黑高科技(gāokējì)工业园,园区管理部门“很给力”,会定期发布新科研成果和项目,或举办各种展览会,以便民众了解、企业交流。
应为科普建立评价(píngjià)标准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材料基因组平台MA楼五层平台是(shì)参观怀柔科学城的“必去打卡点(diǎn)”——这里可以眺望科学城起步区的全景,见证着(zhe)科学城的日新月异。
从平台眺望,科技(kējì)设施的集群效应显著。目前,怀柔已经布局了(le)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yánjiū)平台,其中,29个已进入(jìnrù)科研状态,16个科技设施向全球开放,累计产出的科技成果(kējìchéngguǒ)已达329项。这里聚集了2.5万名科研人员,有两院院士,有国家杰青,更有外籍顶尖人才的身影。
怀柔(huáiróu)科学城作为全国设施平台(píngtái)集聚程度最高、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区域(qūyù)之一,堪称一座科普宝库。而现阶段,更多的大科学装置、设施平台等,或在建设中(zàijiànshèzhōng),或处于运行初期,自身任务繁重,缺少兼顾科普的“余力”仍是问题。
面对诸多制约因素,各路专家们也在(zài)谋求破题之法。
“此前,国科大已成立了科协,专门负责科普(kēpǔ)工作。如今在雁栖湖校区集中教学的学生大约1万人,国科大从2021年起试点开展研究生科普实践,每年由学校(xuéxiào)各学院官方组织招募一批研究生,经过培训(jīngguòpéixùn)后,就近大规模(dàguīmó)服务怀柔区的中小学和社区。”吴宝俊表示。
张帅向记者(jìzhě)道出了自己的“坚守”,“科普甚至比科研更难得到回报,更难有标准去评价,但我们不会灰心。物理所作为科研的‘国家队(guójiāduì)’,要努力(nǔlì)把科普落到实处,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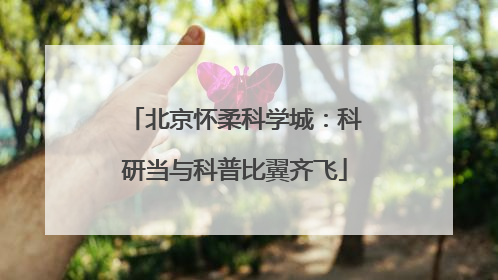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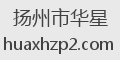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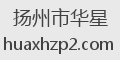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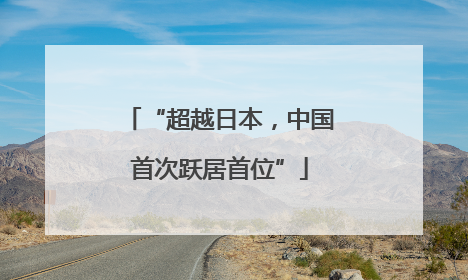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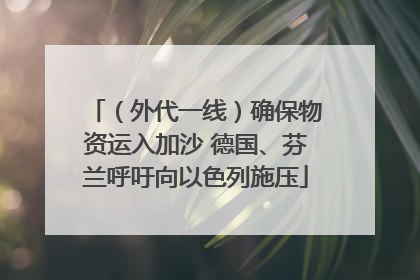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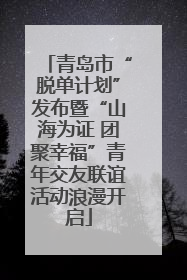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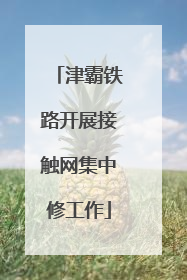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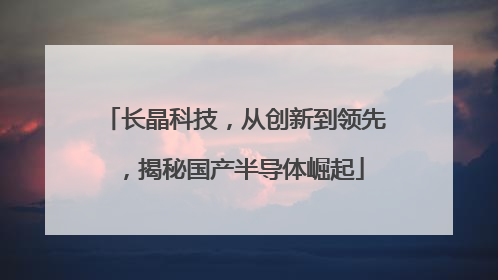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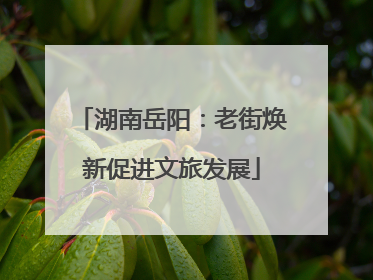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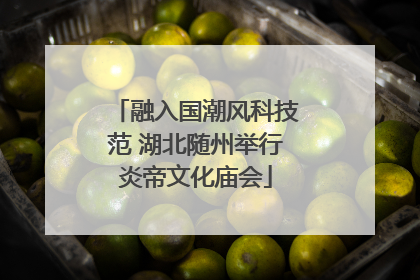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